-
(一)具有2年以上投資經歷,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家庭金融凈資產不低于300萬元;
家庭金融資產不低于500萬元;
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萬元。 -
(二)最近1年末凈資產不低于1000萬元的法人單位。
-
(三)金融管理部門視為合格投資者的其他情形。
3月28日,《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資管新規”)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資管新規即將面世。這對目前總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00萬億元的大資管行業將產生深遠影響。當然,100萬億元可能是注水的數據,剔除交叉持有,資管總金額應在60萬億元左右,這也是一個天量的數字。
我國資管業的異軍突起,有諸多的原因。首先,由于巴塞爾協議二和三對銀行表內業務的嚴格監管,促進了金融創新,導致理財產品和資管計劃的大量出現。其次,從深層次看,資管業的興起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密切關系。過去,中國經濟采用投資拉動和寬松貨幣的政策,大量的貨幣尋求保值增值的出路,資管成為一種剛性需求。再次,資管業滿足了特定行業對資金的特殊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資金配置的效率,提高了金融市場多元化的競爭與效率。
但是,正值資管行業欣欣向榮之時,資管新規卻以迅雷之勢出臺,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概言之,就是“風險的治理”。
第一,防范金融風險是資管新規迅速出臺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任務。2013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組織研究了全球兩次金融大危機,表明高層對于可能的金融危機風險的高度重視。今年召開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將防范金融風險置于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顯然,資管新規的出臺是高層為防范金融風險出臺的一項標志性舉措。
第二,資管行業存在監管亂象,條塊分割,急需統一。由于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各金融行業的監管部門將發展本行業視為己任,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既是貓鼠關系,也是父子關系,扭曲了監管者的角色,競相放松管制,出現了“朝底競爭”的監管怪象。監管不統一,產生了巨大的監管套利空間,這是資管業亂象的根源。2018年,國務院機構調整將保監會并入銀監會,也是統一監管的一步棋。更值得注意的是,資管新規是由央行金融穩定局領頭起草,也表明了高層統一監管的決心。
第三,資管行業存在金融風險的隱患,監管套利嚴重,掩蓋交易實質,架空監管,風險敞露。資管業中普遍存在的“剛性兌付”承諾,對金融機構產生重大的隱患。從交易的實質看,“資管+剛性兌付”的模式,輔以資金池操作,是變相的銀行貸款業務,但是,它逃脫了貸款業務的嚴格監管,沒有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沒有杠桿率的限制,成為沒有監管的大銀行。更為嚴重的是,貸款的去向和用途卻沒有安全保障,在2015年的股災和2016年萬科等上市公司收購案中,大量的資管資金流入風險極大的證券市場投機和上市公司惡意收購中,使得證券市場的風險極易傳導至銀行。
上市公司收購風險極大,美國上世紀70年代,米爾肯(MichaelMilken)通過垃圾債券獲取杠桿資金并購上市公司,之所以稱“垃圾”,風險巨大之謂也,但風險透明,買者自負。我國銀行理財的海量資金,通過資管計劃層層嵌套和資金池的掩護,進入高風險領域,信息卻極不透明,成為監管盲區。最近幾年,剛性兌付紛紛違約,銀行處在較大的風險之中。
1929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就是因為證券市場的風險轉嫁至銀行而引發的,致使40%的銀行關閉,900萬個賬戶因銀行破產而消失,1700萬人口失業。前車之鑒,不得不防。
資管業亂象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我國資管行業基礎法治體系的匱缺。具體來說,由于歷史形成的“金融分業經營和監管”的模式,使得信托法在中國金融實踐中成為一部“小信托法”,就像證券法在中國金融實踐中成為一部“小證券法”一樣,資管行業等諸多金融要地未被作為金融基本法的信托法和證券法覆蓋,成為法治的薄弱之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確立的“金融分業經營”的立法原則,阻止了信托公司從事其他金融業務,但是,未能阻止其他金融機構“侵入”信托業的局面,最終形成了更為嚴重的后果,那就是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行信托之實,否信托之名,逃信托之法”。這就是今日資管界亂象的歷史起源。
在法律上,“資產管理業務”本質上是一種信托法律關系。信托法不僅應適用于信托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也應適用于銀行、證券、保險等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則,如禁止剛性兌付、管理人的信義義務、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禁止大資金池等,本質上都是信托法上的原則。目前,這些信托法原則基本都寫入資管新規中了,可以說,資管新規的多數內容是重申信托法上的基本原則。
從未來執行的層面看,目前尚難判斷資管新規可否徹底改變我國“機構監管”的現狀,實現“功能監管”的變革,但是仍可預期,資管新規在實施中,“朝底競爭”的制度誘因將被大大降低。
當然,此次資管新規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完成一項關于資管行業的基礎立法的工程。其實,在經濟領域的許多新生事物的萌芽和發展過程中,均采取了“先發展、后治理”的戰略,以免新生事物在萌芽之初,就因嚴格治理和監管而被扼殺。所以,互聯網金融、資管業、共享經濟等,均沿著“先發展、后治理”的邏輯生長。但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和監管可能扼殺萌芽中的新生事物,同樣,也可能對發展中的新生事物甚至整個金融格局產生不可預見的影響,這就是“治理的風險”。
比如,我國的金融業是三分江湖的格局,由傳統銀行業、影子銀行和民間借貸三大領域組成,資管新規嚴格治理影子銀行,有可能將資金從影子銀行趕入民間借貸領域。應該看到,近十年來蓬勃發展的影子銀行,為民間資金找到了一條披有合法外衣的投資路徑。雖然影子銀行雁過拔毛,但如果沒有影子銀行,估計影子銀行所吸收的資金會部分轉化為“非法集資”。
總之,全局統籌的金融法治依然是短板,金融亂象不僅需要政策治理,更需要法律治理,走大信托法和大證券法的道路,實現金融治理的統一性和整體性。近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金融開放的重大舉措,中國金融業面臨嚴酷的競爭,中國的金融法治基礎建設就顯得格外重要。資管新規是第一步,今后,在金融開放的驅動下,中國將迎來金融法治建設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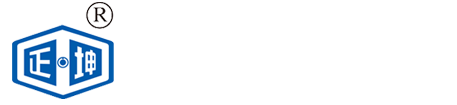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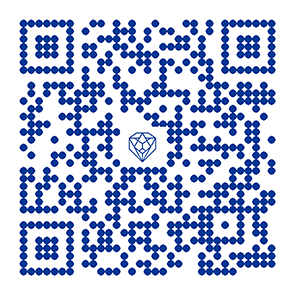





 合格投資者提示
合格投資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