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具有2年以上投資經歷,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家庭金融凈資產不低于300萬元;
家庭金融資產不低于500萬元;
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萬元。 -
(二)最近1年末凈資產不低于1000萬元的法人單位。
-
(三)金融管理部門視為合格投資者的其他情形。
信貸類理財產品在經過2010年政策監管“重拳”的打壓后快速從大眾視野中消失。面對嚴厲的銀信合作監管,銀行把目光投向了“第三方”,延長資金鏈并讓其他機構參與進來。近期媒體爆出的某銀行理財產品不能兌付事件就與第三方理財機構有關。據多家機構觀察,“銀信合作”叫停之后,新的變種已經出現,通過引入“第三方”,信貸資金仍然能夠轉入“表外”。
在2010年8月,銀監會頒布《中國銀監會關于規范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要求信托公司對融資類銀信理財合作業務實行余額比例管理,即融資類業務余額占銀信理財合作業務余額的比例不得高于30%。這是對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重大打擊,從此,以信托貸款、信貸資產、票據資產為投資標的的融資類銀信合作理財產品占比逐步縮小。2010年前7個月,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占比為14%,后5個月降至8.7%。
2010年12月和2011年1月,銀監會又分別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轉讓業務的通知》和《關于進一步規范銀信合作理財業務的通知》,要求融資類銀信合作理財產品中的信托貸款余額以至少每季25%的比例予以壓縮。這導致單一的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數量進一步減少,2011年前10個月,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占比進一步萎縮至不到8%。
“通過信托收益權轉讓的方式進行運作的信貸類理財產品開始出現,該模式的主要運作方式是:銀行先找一家大企業,通過信托發放單一信托貸款給需要資金的企業,然后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去購買這個大企業的信托貸款收益權。在這個過程中,信托還是起了通道作用,實質還是融資,但由于理財資金并沒有委托給信托公司,因此不受銀監會2010年72號文《中國銀監會關于規范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中關于融資類銀信合作理財業務的監管約束。”知名理財專家劉慶香告訴記者。
另外,部分銀行還轉向了委托貸款這類工具,銀行不受讓信托收益權,而受讓委托貸款債權,其運作方式可以概述為:先有一家企業向融資企業發放委托貸款,然后銀行理財產品購買這個委托貸款債權。除此之外,則是由銀行直接募集理財產品,通過委托貸款的形式發放給融資企業,既不占用銀行的信貸額度,又滿足了企業的融資需求。
這類委托貸款操作中,有的是總行作為委托人,分行作為委托貸款的中間方;有的則是分行作為理財產品發行方和委托人,找一些村鎮銀行或者中小銀行作為委托貸款的中間方。
銀行為規避銀監會2010年72號文的要求而創新出的融資類理財業務模式,很快進入監管層的視線。因此,2011年7月,銀監會通過對6家國有銀行、8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廣發銀行、深發展銀行)和1家城市商業銀行(北京銀行)進行監管座談會的方式,通報了當時銀行理財業務中短期化趨勢明顯、規避銀信合作監管新規、變相調節監管指標進行監管套利以及建立資產池類理財產品并通過期限錯配獲得利差等若干重大問題,并發布了《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管座談會會議紀要》。
對于委托貸款類理財產品,會議紀要明確要求商業銀行“不能面向大眾化客戶發行標準化的理財產品募集資金來發放所謂的‘委托貸款’,進行變相的監管套利”,同時不允許商業銀行為委托貸款提供擔保,同時不承擔委托貸款的任何風險。
對于受讓信托收益權類的理財產品,會議紀要要求商業銀行在開展信托受益權類業務時,“應嚴格遵守銀監會關于銀信合作業務的各項相關規定,不得繞過信托公司開展信托受益權業務”。
這一系列監管措施無疑再次將信貸類理財業務的渠道“堵死”,這也使得有關信貸類的理財業務和產品受到了徹底的“打擊”,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單一信貸類理財產品的發行數量急劇下降到24款,更多涉及信貸資產或信托貸款的理財產品被設計成了組合資產投資的方式。
雖然通過信貸類理財業務進行融資的渠道被監管機構層層把關,但是市場的需求以及銀行力圖在中間業務上做大做強的愿望,也使得繼信托渠道之后陸續出現了通過其他渠道進行理財產品融資的創新。
信用證代付業務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創新業務。2011年三季度以來,隨著貼現利率的高位徘徊以及此后票據信托被監管嚴控,銀行承兌匯票業務開始降溫,同樣具備增加保證金存款和逃匿貸款規模功能的國內信用證業務受到了極大關注。與票據貼現普遍高于10%,且一度升至13%~14%的利率水平相比,國內信用證的融資成本一般在8%~9%左右,更易為企業所接受。
對此,劉慶香認為:“對于銀行來說,國內信用證屬代付業務,不占用信貸額度,最低保證金也相對較高。雖然流程更為繁瑣,但銀行也樂意操作。另外,承兌匯票流轉會在銀行體系外,存在一定程度的造假風險,而信用證都在銀行系統內部流轉,相對安全。在此驅動下,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不少銀行的代付業務都出現了爆發式增長,特別是在民間融資需求旺盛的江浙一帶。但是隨著通過信用證隱匿的貸款規模不斷擴大,在大量的信用證代付業務中,有些可能并不存在真實貿易背景,而僅是變相的普通貸款。而借道信托等渠道開展的所謂金融創新也應引起監管層相當程度的重視,否則信貸調控效果可能會遭遇嚴重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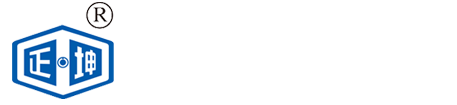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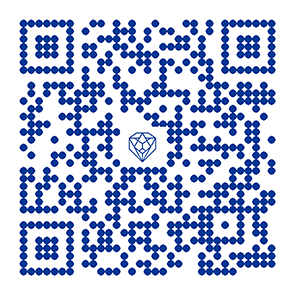





 合格投資者提示
合格投資者提示